您好,歡迎進入安徽省志成建設工程咨詢股份有限公司!
服務熱線:0551-65780607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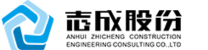


01為什么民企不適合做資產
民營企業未來做資產會非常困難。首先我們先界定,做資產根本是要做優質資產,根據資本估值模型,區位好(cap.rate低)、租金收入好(NOI高)、形象好(品牌效應支持),做資產思路下,民營企業未來面臨著多個層面的問題。
1市場空間缺失
地整體越來越難拿。核心城市對于產業用地控制愈發嚴格,從全國來看,我國一線、二線城市工業用地占城市總建設用地比例顯著較高,工業土地開發效率較低。以上海市為例,上海市工業用地占城市總建筑用地約為30%,而國際一線大城市工業用地占比一般都低于10%,故在上海提出104、195、198用地政策,逐步減少存量低效率工業土地,同時對新增工業用地進行全生命周期監管。雖然上海始終對外表達“對于好項目上海不缺土地”,但要達到好項目的門檻不低。土地越來越難拿是事實情況。
民營企業模式與政策環境不支持。傳統產業勾地,地產覆蓋持有資產沉淀的模式受阻。從現在市場情況來看,具備優質資產或未來優質資產屬性的一線、二線、強三線城市基本已無地可勾。M0等新型產業用地的出現,產業發展與獲地高度綁定,民營企業自身產業發展能力缺乏長周期理念,且在未來土地分批供應的趨勢下,對于片區土地出讓的“控地能力”顯著弱于國資企業,進一步使得民營企業的傳統模式發展愈發困難。從我們長期市場走訪來看,2019年末開始,多家民營企業都要求可售完全覆蓋持有方能投資,而這種土地要符合未來優質資產屬性,幾乎無地可找。
融資環境不支持民營企業重資產沉淀。不做勾地,不做地產覆蓋,就意味著資金沉淀,高基礎利率環境下,國內做資產的長線資金缺失,資金沉淀幾乎是不可承受之重。2018年6月,海外資金原則上只能存量替代借新還舊,不能新增。這產生了“關門效應”,民營企業重資產沉淀業務全面受阻,在2018年6月前已經發行海外債的尚有騰挪空間,未發行海外債的則無力支持。而真正低利率的海外保險資金、養老資金,對于NPI/COST指標達到12%-15%,僅有少數資產可達到相應回報率要求。
2發展條件缺失
可以建設優質資產的往往基本需要通過并購或合作開發。以金地威新為例,其多個標桿項目(深圳威新軟件園、上海8號橋、上海閔行科技園)通過并購或合作開發獲得。
首先,民營企業找不到人,很難充足撬動資源。存量土地往往掌握在區域資源主手中,“區域屬地化合伙人”角色是開發的前提。即區域熟悉政府政策、有招商資源、有一定區域資源的“人”是獲取的前提條件,往往來自區域同業企業的高管或區域政府招商局領導,且“人”需高能級,否則無法撬動開發的必要資源。這類“屬地化合伙人”央企國資更能驅動(如招商蛇口在區域上早期持續使用合伙思路整合資源),而民營企業整合能力較差(華夏幸福也采用了類似策略,但人的能級顯著下降,最終導致項目推進存在問題),獲取“屬地化合伙人”對民營企業人事工作提出了較大的挑戰。
其次,身份不占優勢,發展騰挪空間較小。相當一部分存量土地其實掌握在國資企業手中,資產并購涉及國有資產問題困難重重、民營企業合作開發存在現金流思路問題(如市場不好是否能降價等),相當一部分國企靠著國企的牌子是獲取高性價比的“優質資產”的重要條件。相對于國資企業可以相政府要政策支持,要其他相關業務作為騰挪或交換條件,這邊業務的沉淀與虧損可以通過其他業務做補償(中交、中建的傳統套路),民營企業往往只能就業務談業務,且與政府方面缺乏互信。總的來說,對于傳統住宅公開市場招拍掛,民營企業可以通過機制獲取優勢,而在產業地產領域,民營企業在拿地層面身份不占優勢。
第三,“民營企業做資產”誰來做和怎么管的問題突出。首先來看“誰來做”的問題。從行業結構來看,民營企業中規模化的房企戰略性發展產業地產業務,方有可能去接受優質資產可能產生的沉淀,但房地產企業“三道紅線”要求下,光有融資能力是無法滿足監管要求的(如龍湖商業依托于融資的發展模式)。在具體業務方面,從近幾年來看,大量比較有想法的企業往往是排名20-50的房企,這批企業排名提升基本是通過2014-19年高周轉沖規模得來,而這些企業的“三道紅線”問題又是最突出的,企業產業板塊更是被必然被叫停,這都最終形成了“民營企業做資產”誰來做的問題突出。其次來看“怎么管”的問題。產業板塊盈利始終不及地產,一方面,及時企業戰略性投入存在“度”和“決策搖擺”的問題,另一方面,長時間的業務收益相差太大勢必造成內部人才流動問題,優秀的人才一定會向高收入的區間流動,而持續補貼往往會造成企業內部管理上的不滿,亦或是其他管理問題。這些問題并非不能解決,但組織結構上設計思路的不完善往往會導致業務的崩潰。
02國資企業不適合做服務
國企做服務是非常困難的。縱觀產業地產行業,除了張江高科與天安數碼城(也不能算完全的國資企業),其他帶國資企業基因的在服務方面基本發展都沒有太多亮點。反而是一批輕資產運營類的企業,例如,中城新產業能為園區企業真正去找業務、嫁接資源,雖然落地成效還待檢驗,但理念與概念在行業中還是走在比較領先的位置的。例如,浙江省部分專業的民營園區,園區已經變成一個供應鏈公司,園內企業作為供應鏈上的一環,進行深度的服務和發展。
反過來,我們看張江高科和天安數碼城為企業提供的服務,其實是具備非常顯著的國資特征。即,基礎的、平臺類的是國資通過自身努力尚可達到的領域,而真正為企業一對一定制服務,對于細節把控和深入企業運營還得民營企業來做。以張江高科為例,張江的園區服務主要是平臺業務,例如“投貸聯動、895訓練營”等,主要是基于自身區域優勢,為企業與資本構建平臺,進而實現服務。而張江自身科技投行的理念,其根本有多重的歷史因素,一方面早年招商目標下的投入,發展周期下使得自身本身有收益,而企業提出科技投行戰略更多是一個順過去趨勢,承接現在優勢(園內生物醫藥、集成電路產業的成熟)的發展方向。而真正從企業細致服務而言,張江表現其實并不突出,而其投行效率現階段看來也有下降的趨勢。以天安數碼城為例,天安數碼城對于小微企業的服務表現突出,但天安對于小微企業的服務還更多的是套路性的,標準化的解決小微企業的固定需求,不能真正的通過運營帶動片區產業的發展。
究其根本,產城服務也好,園區服務也好,影響國資與民營企業真正的區別在于“鏈接”。服務的未來一定在于資源的鏈接,國資企業可以平臺,但最后服務于企業的鏈接還是需要企業自己去走完,國資企業在標準化的基礎服務上可以花很大力氣去做好,對針對一些有變通需求的企業實際要求,則往往存在難點。實現“鏈接”的根本在靈活的利益分配,國資分配機制不夠靈活、人員配置機制不靈活是無法實現真正貼身服務的根本。而民營企業在分配機制,人員機制上的靈活,使得企業可以更好的鏈接相關資源。但對于服務方面民營企業自身資源有限,平臺難以建立等問題客觀存在。未來民營企業可以依托于國資的一些平臺,做最后一公里服務,實現自身價值的創造,這將是未來發展趨勢。
03產城未來:國企做資產,民企做服務
基于企業自身基因與稟賦分析,我們理解“國企做資產,民企做服務”,大型國資與優質民營企業的深度合作將是行業未來。混改太遠,合作很近,各取所長,以合適的機制創造價值將是未來。